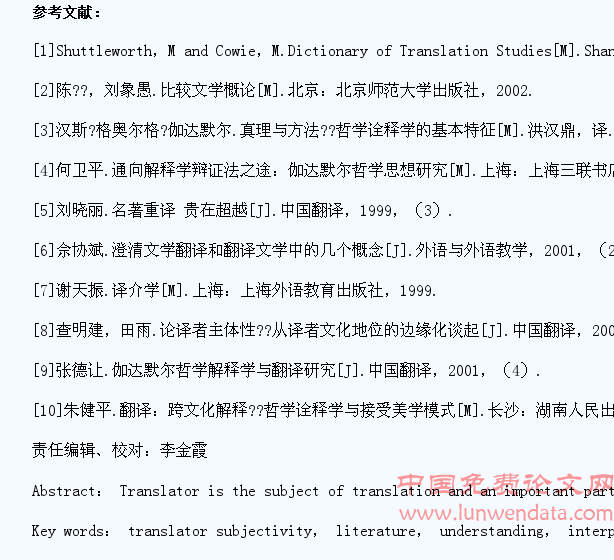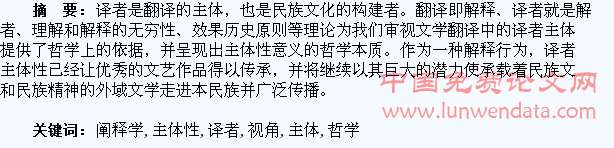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1573(2015)01-0030-03
关于译者主体性,查明建等(2003)觉得,“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首要条件下,为达成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点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主要代表伽达默尔,直接继承和进步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理论,打造了哲学阐释学。在其看法中,翻译即讲解、译者就是讲解者、理解和讲解的无穷性、成效历史原则等理论为大家审视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并呈现出主体性意义的哲学本质。
1、永恒的阐释:文学作品的传承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看法觉得:理解永远是相对的,阐释学循环也从来不会停止,由于人的有限性和历史性使得讲解行为既没起点又没终点。它就是人类存活活动本身,由于人类存活本身就是一个从不间断的阐释过程,而理解是人的存在方法,生生不息(何卫平,2001:
162)。翻译就是讲解,一种以理解为基础的讲解。依据伽达默尔的看法,既然讲解发生在熟知性和陌生性之间,那样每个年代势必以它我们的方法来理解一个文本。
伽达默尔在其著作《真理与办法》中对“节日”进行了探讨和类比。大家都知道,一个节日没庆祝是不可以进步的,只有经过庆祝,节日才会存在并延续下来,也就是说,庆祝者的参与是节日存在的首要条件。假如节日的那天无人来庆祝,那样节日也就成了一个虚无的名字。节日年复一年地举行,没了这个循环,节日也就会不复存在。节日的本质和内涵在一年一年的循环中不断地被理解和讲解。同样,文学作品的长久存在也在于被不断地阅读和理解。文静作品是“永恒的目前”,它们永恒地面对和历程着不同年代不同大家的理解和讲解,这就是它们的永恒性。但,无论置于什么年代,一部文学作品总有其不变的内容,就好比节日年年庆祝、每次庆祝都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但节日依旧是同一个节日。
一部文学作品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开始历程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理解和讲解。一部《红楼梦》可以看作政治小说、伦理小说、道德小说、社会小说;《水浒传》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小说、政治小说和虚无党小说(陈??,刘象愚,2002:
146)。《哈姆雷特》在历经三个世纪的阅读和舞台表演后,依旧是不朽的经典。即使是今天的年代,对这部名著也有着多元化的理解和讲解,冯小刚的影片《夜宴》就是在《哈姆雷特》的基础上改编成的中国故事。正是通过大家永恒的讲解,文学作品才得以传承到了今天,并继续传向以后的一代又一代。大众所熟悉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在历程了不同年代的电视版本后,依旧是可以吸引不同年代观众的不朽经典。中国本民族的文学作品通过语内讲解而得以传承,而域外的文学作品则是通过译者的跨语言和跨文解决释在国内传播,譬如《哈姆雷特》,通过林纾、朱生豪、孙大雨和卞之琳等译者名家的讲解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
翻译就是讲解,而译者就是一位讲解者。作为一种讲解行为,译者的主体性已经让出色的文静作品得以传承,并将继续以其巨大的潜力使承载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外域文学走进本民族并广泛传播。
2、理解和讲解之后:翻译文学的打造
译者主体性的要紧意义之一,还在于它是翻译文学得以开始并逐步打造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图里觉得,译语文本是以先前存在于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为基础的,其特质更多地遭到译入语文化的决定和制约,而不是主要决定于源语文本和所谓的翻译程序(Mark Shuttleworth和Moira Cowie,2004:
165)。
非常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对于文学翻译持有偏见,一直认为文学翻译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语言转换。过去有一种误解觉得,任何一个人,只须学会了一门外语并有一本双语词典,就能胜任文学翻译的重任。这类人看不到,当然也不会承认文学翻译过程中所蕴含的译者所作的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因而也就看不到文学翻译作品的相对独立的美学和艺术价值。因为误解的存在,文学译者和翻译文学本身都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前者在民族文学史上没地位可言,而后者也同样没我们的地位。
谢天振教授在其著作《译介学》中提到:从文学研究和译介学的角度来看,文学翻译有其要紧的意义,即,文学翻译是文学创造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就具备了它们独立的艺术价值。
因为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外域文学作品被赋予了独特的艺术魔力,并用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和内容长久吸引着译文读者。文学译作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价值就是它们可以进入民族文学的范围,并在丰富和进步民族文学方面起着要紧用途。一部文学作品越是出色,其所蕴含的艺术内涵也就越是丰富,译者对其的讲解(翻译)也就越是多元化。冯明慧曾提到过,“一部好的译作是原作的来世,并非所有些人们都能知道所有些文学作品,更不是所有些人们都可以胜任翻译工作。一个好的译者可以克服文学作品的种种局限原因并赋予原作一个新的生命。译者的工作使原作可以面对新的读者群体,并将原文作者要表达的内容告诉新的读者们”(谢天振,1999:233)。
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本身的一种存在形式,可以从水平、水平和影响力几个方面进行评价。比如,将巴尔扎克使用方法语写就的小说《高老头》翻译成中文可以被称作“文学翻译”,但由傅雷用中文翻译的译作《高老头》就是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由于中文版的《高老头》已经是原作品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更具体地说,一部翻译文学作品是从早已写成的作品(原作)中派生出来的作品,也是一种依靠于原作却又不同于原作的作品。所以,原作品是外域文学,但译作应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存在形式。
1989年,陈玉刚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纲》明确叙述:“翻译文学是世界文学的要紧组成部分,中国的翻译文学是国家文学范围里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转引自佘协斌,2001:54)。 从哲学阐释学来讲,译语文本是译者对源语文本进行理解和讲解的成就,而译语文本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和健全后确定下来,就成了翻译文学。由此可以证明,翻译文学是无数翻译专家和学者长期不懈奋斗和创造性劳动的产物,也是译者对外国文学一丝不苟进行理解和讲解的成就。因而,在文学翻译这条联结原文和译文的漫长道路上,译者主体性的意义之一就是它在翻译文学的形成、传播和打造方面所作出的极具价值的贡献。
3、文学作品的复译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的复译这一范围也发挥着要紧用途。
伽达默尔在其哲学阐释学中对“成效历史”的讲解能够帮助大家理解文学作品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是和理解者一块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伽达默尔将这种过程历史称为“成效历史”。成效历史原则强调要在艺术作品的成效历史中理解作品本身,如此就把历史和目前联系了起来,也就充分展示出历史文本对于当下社会的意义。“一部文学巨著就好似一座丰富的矿藏,不可能通过一次或两次的讲解就穷尽其意义。任何一个译作都是对原文意义的挖掘……正是通过连续不断地讲解,大家才可能接近对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的完全理解。从文本本身来讲,一部文学作品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确定下来,但译者的美学观念、价值观念与他/她们的语言却是伴随年代不断地在变化。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拥有合适于年代变化的译本,是非常有必要的”(张德让,2001:25)。正由于这样,文学名著如《红与黑》《唐璜》和《简?爱》在中国分别拥有十个以上的译本,其中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译本都带有深刻的不同年代的印记。
文学作品的诞生与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干扰可以表明社会方面对其的认同,同样,译作也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原作在源语社会的影响力可以持续上百甚至上千年,但译作在译入语社会中未必享有同样的地位,由于源语读者群体在理解他们的当地文学方面没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虽然作品当中所反映的文化会因年代不同而变化,但这不会为源语读者群体导致太大的困难,由于他们对自己民族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有着继承性。但译作则不同,由于译入语读者和原文作品没继承关系,伴随时间的推移,旧的译作版本不再适应新的年代,势必被新的译文版本所替代。不难想象,一百年前很时尚的译本到如今还是不是能同样受青睐。翻译包含“从书面文本到图画(电影,电视等)”如此的形式(朱健平,2007:
195),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从书面文本到电视改编”和“从英语到中文”是一样的,从哲学阐释学角度来讲,两者都是对原文文本的讲解,那样,大家就能看到,《射雕英雄传》在不同年代的电视版本与《红楼梦》和《西游记》的重拍可以从一个生动的角度反映出文学作品复译的不可防止。
在对《呼啸山庄》的三个译本进行比较剖析后,刘晓丽得出如下结论:(1)复译体现了对原作愈加深刻的理解和领会;(2)复译体现了对原作风格和精髓的更趋适当的把握;(3)复译使得译文语言更符合当代读者的审美期待(刘晓丽,1999:
12-16)。译者的努力使《呼啸山庄》在中国与时俱进;译者主体性赋予了原作在译入语社会中的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来世”。文学译者的复译使出色的作品在异域的环境中得以长久地存在。
世界上有不朽的原文,但没不朽的译文。在文学作品的复译中,译者所作的绝不应该是无用的重复,而是富有意义的再创造。时间会淘汰掉不好的译作,而译者的创造性努力会产生出新的译作,这类译作使出色的外域文学作品在目的语文化和社会中长久传承。
4、结束语
著名翻译学者根茨勒过去指出,翻译中所有些问题都可以从哲学的立场看得愈加了解。朱健平也提到,“翻译研究的最高层次应该是对翻译现象展开哲学考虑”(朱健平,2007:41),那样,作为近几年来翻译理论界所关注的话题,译者主体性同样可以从哲学的视角来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为译者主体性的意义提供了肯定的理据:理解和讲解是永恒存在的,所以译者对文学作品不断地理解和讲解(翻译),使得文学作品能在新的环境里传承;经过长久的积淀,译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讲解会演变为某个年代的经典文学创作,这就是翻译文学得以发生和打造的基础;成效历史原则强调从艺术作品的成效历史中理解作品,文本的意义是和理解者一块处于不断生成之中的,所以一个译本只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临时固定的,而且,人类会在持续的理解中超越自己,译者作为讲解者,也会在不断更新进步的“成效历史”中对文学原作进行新的讲解,创造出新的译本来适应年代的变迁。